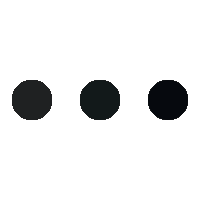新歌难觅、曝光量减少,除了早期的名曲外,腾格尔推新歌和发新唱片的节奏放慢了,观众对腾格尔的记忆总是保留在《天堂》、《蒙古人》的辉煌年代。面对唱片业“制作人转行卖烤鸭”的惨淡现状、面对逐渐增长的年纪,接受记者采访时,快52岁的腾格尔却冷静而理性。腾格尔感慨道,现在连推新歌都难了,更别说发新唱片:“最近我有首歌叫《心的归宿》,非常好,应该说是很牛的一首歌。可是推出来太难了。”
至于原因,腾格尔归结于整个音乐圈的风气,他批评很多原生态歌手太过注重视觉表现力了,演唱反而变得不重要,而他觉得一个歌手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要把歌唱好:“现在音乐圈比较浮躁。我一直认为唱歌是以歌声来打动人,用你的情感来打动人,而不是用一些华丽的东西来打动。而现在不一样,人们注重的是华丽的东西,至于歌唱得好不好是次要的,形式大于内容。音乐它应该是一种听觉的东西,但现在不是。现在感觉音乐是视觉的,你得看。很多人说大众喜欢,但是大众只是一方面,包括圈内人、制作人、电视台,他们都需要华丽的东西。”
“我不想藏着任何作品,我想把好听的歌都推出来,但是难,难就难在这。”说到激动处,腾格尔表示,他的音乐没有华丽的东西,因此与现在的音乐圈的流行“格格不入”:“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的《心的归宿》出来就比较难了。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。我的好多歌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种静的享受。因为现在人很忙、非常浮躁,天天忙,那么当你很累的时候,听我的歌,可以让你休息一会儿,把你的生活节奏慢下来。或者你们在城市里很忙的时候,我的歌就呼唤你到草原上、到宽广的地方休息一会儿。可是现在的音乐不是这样,而是玩命地给你上发条,你紧张,我让你更紧张。”
因为感觉音乐圈子比较浮躁,腾格尔甚至萌生了退意:“我跟公司、跟团里面也说,今年开始少给我安排点演出。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感觉我的音乐好像格格不入。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应该慢慢地淡出。”
人到中年,腾格尔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活得更加实在,好歌唱给朋友听,自己掏钱把歌在棚里录好,放在家里,有朋友来了就一起欣赏。相比演出、出唱片,他更喜欢小众圈子内赏玩音乐:“打新歌、出新唱片不是我该做的事,这是那些急于出名的乐坛新手该忙的事,我现在不需要再增加名声了。”
“人不服老不行。” 腾格尔表示,去年重新录歌的时候他发现10年前的高音他已经唱不上去了。他已经考虑慢慢收山,今后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家庭上。
腾格尔还说,他已经不复10年前那个自觉对民族音乐有责任心的自己,现在的心境是不想再为中国音乐“瞎担心”:“你们浮躁你们的,我做我的。原来大概10年前,我有过这样的想法,中国的民族音乐怎么发展,我认为我有责任。我曾经这样想过、这样考虑过。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了,感觉好像是瞎担心。”说完,腾格尔又补充了一句:“有时候可能也考虑不了太多。”
不过,在采访中,腾格尔否认了自己是因为音乐市场不景气才投身拍电影,只不过看了太多烂片才萌生自己动手拍一部电影的想法,另外也是因为中了朋友的“激将法”:“演电影跟音乐市场没关系。以前跟朋友一起看电影的时候,总是经常感慨发出各种议论,好的不好的说一大堆。后来就被朋友说你牛!那你拍一个啊,我就一口回说,行啊,拍一个就拍一个。正巧遇到了《双城计中计》这个剧本,就是这么被激将拍了这部电影。”
腾格尔在讲述两个江湖老千前往戈壁大漠抢日本人黄金的《双城计中计》中出演一个江湖大骗子“不动石佛”,与大家对他的以往印象大相径庭,腾格尔说,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:“当初想好了,拍电影有两种角色不拍。一个是音乐人角色不拍,一个是蒙古人不拍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蒙古歌手,既然演戏,就要演一个跟自己截然不同的。”
面对任贤齐、翁虹等合作者,第一次演戏的腾格尔毫不介意称自己属于本色出演:“熊乃瑾说我像个20多岁的大男孩,很腼腆又很简单,她说看我演跟小齐打架的戏一直笑场,拍了六条笑了六次。我很奇怪,女孩子看男人打架怎么会笑呢?我是不会表演只好本色出演,他们都说我演得特别搞笑,特别萌,我觉得能让大家开心,很好啊!她叫我萌帝,我得谢谢她。”
超过20年的歌者生活,让腾格尔养成了固定的作息习惯,冷不丁开始拍戏,让他很不适应,剧组经常拍到天亮收工,有一段时间基本每天拍到早上五六点。另外,《双城计中计》在风沙漫天的大西北取景,不出几天所有人都晒得黝黑。
在感受过风吹日晒的剧组生活以及连续拍夜戏的辛苦和紧张之后,腾格尔宣称,《双城计中计》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:“最大的困难就是化妆。我是一个唱了几十年歌、上电视从来不化妆的人。每天在剧组里拍完戏卸妆的时候,真的是从第一天开始数,一天天感觉度日如年。表演是一门艺术,《双城计中计》一次尝试就够了。我不是学这个的。其实《双城计中计》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次正式的电影作品。以后不拍了。”